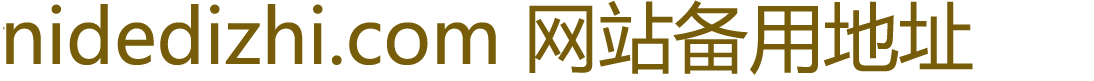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籠之五 逃亡
「零月明白的。」零月睡在客房,現在的她睡在床上,背著他,面向米白色的牆壁。零月平靜的說:「您不用擔心零月。」
怎能不擔心?零月的纖細的雙肩在抖顫。
「妳不舒服嗎?」見她沒回答,劉昇影抓起了她的肩,將她翻過身,面向他。
瞥見零月的俏臉上掛著兩行晶瑩剔透的淚珠。
「妳怎麼了?」劉昇影問:「想著什麼嗎?」
「零月覺得好難過--」
那是無形的桎梏,她以為自己已經擺脫了,其實不然。
「是環境變了,妳不適應這裡嗎?」劉昇影再問。
「不是的。」零月說。
「零月想起凌子舜先生,就感到悽愴。」熱淚凝睫。
「怎麼?妳今天不是帶笑的渡過嗎?一天將盡,妳怎會在最後以淚水破壞了原來美好的一天?」劉昇影用嘶啞的聲音問。
他想做的事情無非是想她快樂,如今,她的淚令他感到挫敗。
簡單如想守護一個人的笑容也做不到嗎?
零月在被窩中抽泣著。
他問:「妳捨不得凌子舜嗎?」
不要再說那個名字了!他一說,她心就揪痛。
零月沒有回答。
「嗯?零月?」劉昇影乾脆扶起她,讓他看見她臉上表情。
現在的她滿臉淚水。
「還是說,凌子舜對妳做過什麼?」他放輕語氣問。
乍然聽此語,零月張著驚惶的兩眼,刻意閉鎖的回憶像潮水般向她湧來。
零月的櫻唇在顫抖。
「嗯?」他問。
零月的眼睛流轉著悽苦。
良久,良久,軟弱的話語自她雙唇間吐出了--
「零月記得,那天--凌子舜先生他進入了零月的身體--」
幕幕記憶在腦海中播放,零月恐懼的說:「好痛、好痛、零月的全身似被攪碎--」
心碎成千萬片。就似重新經歷一樣,零月緊縮身子,掩著臉,淚水,就不曾停止過。
「零月好痛--某處傳來劇痛--零月不斷叫痛,但是,凌子舜先生沒有理會零月--他只是不停侵入零月的體內--」
卑劣的傢伙!劉昇影一聽,憤怒令他身子緊繃著。
劉昇影聽著,聽著,心中就顫慄。
他眼看零月在他面前徹底地崩潰。
室內,是零月細微的抽氣聲。
零月泣不成聲,好一會兒才平復過來。
她說:「零月不懂發生了什麼事,那幾天,零月的心擰痛,眼睛內,有液體流出來,就像現在一樣。」
她停了一下,說:「可是,零月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這一些是眼淚,」劉昇影用手擦拭零月的淚水。「人的淚水,在傷心時,開心時,也會流出。不過,我相信,零月妳當時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傷心了,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眼淚。」
零月聽了,悲從中來,淚水就再度不自控的決堤。
劉昇影緊抱零月,讓她盡情的流淚,直到她疲倦至入睡。
夜深了。
22:58
24/6/2010
零月明顯是九型人格中的第五型-_-
我想看留言啊啊啊啊啊
*
張開眼睛,只見劉昇影躺在她身旁,他的兩臀仍環抱著她。
「不好意思,昨天零月失態了。」零月說。
劉昇影說:「不要緊。妳睡得很熟,我不想打擾妳。」
「哭過後,心緒有變得輕鬆一點了嗎?」劉昇影問。
「嗯。」零月的臉兒上仰。「已經好很多了。」
要枕著別人的手整天,零月實在過意不去:「劉昇影先生,您的手不會痠嗎?」
「不會。」劉昇影說。
他說:「今天我們到遠一點的地方,要到別的區域去。」
零月說:「那起行吧。」
*
「飛船?」零月問。
劉昇影說:「它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所謂的飛船,是一個龐大的飛行物,外表跟郵輛相近。
一輛飛船可容納六十人,通往溫室內不同區域。
劉昇影從口袋中掏出一張通行證,對零月說:「拿著,是飛船的票。」
零月接過票。
入口的玻璃門在兩人面前滑開。
登上琥珀色的飛船後,兩人挑了一列近窗的座位安坐。
不一會,飛船像汽球一樣飄上天空。
零月遙望城市的風景,市內景觀一望無際。
飛船遠離市區,越過一段荒地。
兩個小時後,飛船徐徐降落,兩人到達一個小鎮。
劉昇影說:「這兒是個不起眼的小鎮,很少人會專程來到。」
零月問:「我看過飛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