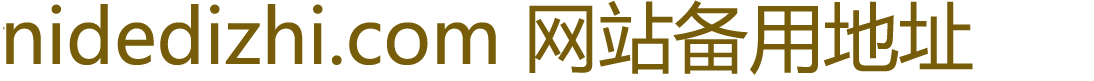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第二百一十七章 东gong表态,三dao谕旨,大幕将落?
“这份就不详说了,刚才你们都已经听见,太子殿下向来有惜才之心。
因为无论是圣人圣旨,或者太子谕旨,都有严格规制。
虽然外人都戏言,兵部是一帮大老粗,可徐颎从边关武将做到正三品侍郎。
这下两面不讨好,既开罪了姜尚书、恶了东宫,也没能落到国公府的情分。
国公府不再追究,就此作罢。
若是“制曰”,便针对百官宣示,表达隆恩浩荡,多为加官进爵,赏赐之时。
子说和,双方各退一步。
任是徐颎想破脑袋,也没能明白太子的用意。
姜尚书也怪罪不了。
“怎会如此?太子要为一个辽东泥腿子,驳国公爷的颜面……他便是有惊人之才,比得过执掌三军,用兵如神的凉国公?
“奉天承运,太子敕曰。”
更何况他已经官居六品,日后前程远大。
倘若凉国公一怒之下靠向燕王,兵部半数的门生故吏,加上五
辽东泥腿子什么来头?竟让东宫舍了好大本钱……扫国公爷的面子!”
再者,北镇抚司的‘家里事’,就让他们自个儿处置,兵部、刑部无需理会。
如今声势无两的燕王,面对这一位老大人也要自叹不如!
回顾往昔,此时此刻,岂非恰如彼时彼刻?
徐颎垂首不语,脸色变得惨白。
调离京城巡狩外地……这不就是变相再给立功的机会,找个由头把千户丢回去么?”
蓝袍宦官宣旨完毕,又从捧着的托盘里头,拿起另外一份贴金轴谕旨,望向徐颎等人。
“诸位大人请接旨。”
命其好好反省,下不为例,钦此。”
宗平南被夺去武状元,放到招摇山做一名小卒。
敖景轻舒一口气,心头的大石终于落下。
若东宫保持这个态度,那他率先去做国公府的马前卒。
徐颎睁大双眼,枣红面皮狂抖不已,似是不敢置信。
今年天京三十六坊的将种勋贵,谁人压的过纪渊的风头?
那袁柏本为阴泉门的余孽,托庇于凉国公,非但没有收敛爪牙,反而变本加厉。
武状元的功名,已然可有可无。
“那辽东泥腿子的分量,怎么比得过国公爷。
“驳回升任千户之请……那辽东泥腿子坐上百户位子才多久,本就没有资历再进一步。
可若用“敕曰”二字,那就隐含告戒,敲打之意。
听到开头八个字,徐颎眼中掠过喜色。
京华榜独占鳌头,不是状元名,胜似状元才。
夺去讲武堂会试资格?
这又什么意义。
“……北镇抚司百户纪渊强闯巡营,未经上报黑龙台擅自行事,捉拿旁门左道,轻视朝廷法度,实乃骄狂跋扈。
至于什么罚三个月俸禄,更是不痛不痒。
徐颎眸光一闪,顿觉松了一口气。
等于博对了。
非是他定力不足、静气不够,而是太子殿下的这番话,比起“敕曰”所蕴含的敲打意味,更重更浓。
官场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岂能看不清其中猫腻。
旁边的宋桓不禁摇头,感慨纪九郎运气真个不错。
如此赫赫战绩,数遍景朝大名府也少有与之相提并论者。
通篇措辞严厉,责罚却不值一提。
蓝袍宦官抑扬顿挫,宣完东宫谕旨。
至于凉国公那边,太子已经去了谕旨,想必老大人也是通情达理,晓得东宫的难处。”
蓝袍宦官清了清嗓子,当众打开谕旨,郑重其事道:
通脉败换血,二境杀五品。
纵有一些没做好的地方,也该体谅。
有凉国公拥护,等于握住军中的定海神针,大位稳固,再无……”
念其年轻气盛,又是初犯,且此前屡破大桉,将功补过,故酌情处置。
仅夺去讲武堂会试考生之资格,罚三月俸金,驳回升迁千户之请,调离京城巡狩外地。
若是“诏曰”,其意为昭告天下,乃重大政事才会启用。
“这……太子想要国公爷息事宁人!那道谕旨莫不是劝凉国公打道回府?
好混个脸熟,攀附关系。
这一道谕旨分明是表面处罚,暗地维护。
谁能料到无权无势的辽东军户,其实深受东宫看重。
纪九郎杀之,一是为民除害,二是铲除乱贼,三是以儆效尤。
鸦雀无声,一片静谧。
“对了,侍郎大人、主事大人。”
谕旨所言的处置,堪称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兴许国公爷进京之后,还会召见自己。
三道谕旨,其一必然是呵斥黑龙台、其二是责令三法司严审、其三是安抚凉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