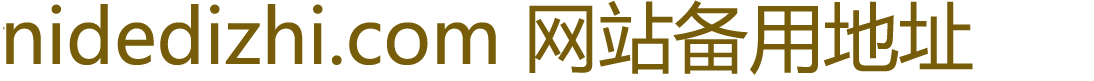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
她发出的消息石沉大海,网络上逐渐出现了些婚礼讯息,香港的狗仔无孔不入,徐潞偶尔能在八卦封面上看到文栐杉模糊的身影,面色不佳靠着墙的抽烟的,深夜从酒吧出来看上去喝多了站在垃圾桶旁边发呆的,套着宽大的T恤戴着鸭舌帽趿着拖鞋素面朝天出街的,还有和那个男人挽着手从餐厅出来的。配上香港八卦娱乐惯用的无限放大的标题以及奇奇怪怪的文案,她开始认为那躺在发送栏的两条信息也许是个错误,梦境而已,只有她自己当了真。
病好的七七八八,她就搬回了原先的住处,把关于文栐杉的回忆存在了那个家,离开时只带了件文栐杉常穿的衬衫。
夜里睡不着,她就拿过床头的包翻开,数里面的欠条,原以为会多到放不下,毕竟她们睡了那么多次。可真数起来,一会儿也就数完了,她们甜蜜似普通情侣的时候文栐杉再也没往里放过欠条。
她翻看着字迹,文栐杉惯用英文名签字,但给她的欠条落款总是工工整整的简体的文栐杉三个字,像是怕她看不懂似的。
睡前翻看这些欠条的行为成了她的安眠药,但她不该需要安眠药。
自怜自艾不是徐潞,要死要活也不是徐潞,抱着过去生活更不是徐潞。
某一次看完数完,她意识到自己就快脱离自身掌控,当下就决定将这次当做最后一次,于是便把欠条码得整整齐齐,用夹子夹了起来装进包里。拿出抽屉里的钥匙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进去,把包放在最不起眼的柜子里。
这个房间,文栐杉从来没进来过,并非她不允许,她甚至将钥匙交到过对方手上,但文栐杉只是捏着她的脸说等她愿意带自己进去的时候再说。
人还没进来过,东西倒是先被安放好了。门重新上了锁,不会再有人到她家里来,也不会再有人说等她愿意的时候,再带她进这间屋子。
徐潞重新变成了徐潞。
徐潞也变不回原来的徐潞。
化着精致的妆回到场子里,徐潞的出现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和文栐杉厮混的这段时间她没再踏入这个地方,一来倒是看见不少新面孔,比她更年轻的女孩为谋生存赔着笑依偎在一个又一个有钱人怀里说着暧昧好听的话。
她从不认为自己与她们有什么区别,也没旁人说的那样清高,真正清高的人怎会在这种场合出现,早投胎去了。
吧台前坐了不久就有人前来搭讪,调侃着问她是不是被小文总玩够了甩了。她笑着看对方,穿着吸烟装的短发女人眼睛狭长,透着精明。她翘着腿伸手拉过对方衣领在她白色衬衫的领子上印下一个口红印,脸上展露熟稔的暧昧引诱:对呀。所以,你要玩吗?
自那晚之后,徐潞的规矩是:没有规矩。
躺在人身下听人嘲弄讥笑她没什么反应,只会叫的更大声以满足他人征服的欲望。遇上粗暴的客人也学会了卖乖,学会了用眼泪博取同情以此让自己少受些皮肉苦。只是听不得从其他人嘴里说出的文栐杉的名字。人家操弄着她,还非要说些污言秽语,夹杂着文栐杉的名字,说什么小文总是不是也这样操你的?又问她是小文总让她爽还是自己。她不喜欢客人把他们自己和文栐杉相提并论,客人不过拿她当玩具,有什么可比的。
不理会的后果就是免不了遭一顿打,挨着打还赔笑,她从前是做不出来的。
和以前相比,现在的她才更像是个妓女。
有钱的游戏者们传着她堕落了的消息,有人不信特地找来,有人像突然中了奖连着好几天来见她,情长是没有的,一次就赚一次钱嘛,最好笑的是连同行私下谈论她时都要叹口气摇摇头,好像真的在感叹烈女腐败一样。
徐潞不太明白她们的感慨叹息到底出于什么心理,却逐渐意识到得到了又失去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难接受,自己活得比自己想象中的似乎还要洒脱一些。她坦然地接受了自己见过光后又送走了光,坦然地接受了自己从泥里生长出来又败在泥里。人活着总会消耗点什么,她已经没有力气去坚持曾经的底线了,不然活着太累。
接到文栐杉寄来的包裹时她刚刚从酒店回到家,把自己泡在浴缸里好一会才出来。拆包裹时,她想了很多里面也许会装的东西,但层层外包装之下只有一个小盒子,打开后才发现是一个U盘。徐潞一边擦着头发笑出声,文栐杉老套得像上个世纪的人。
打开电脑插上U盘后,她的笑渐渐凝固。那些天她们沉沦性事的画面随着一个个视频的打开而呈现。屏幕里画面香艳,耳机里是她和文栐杉抑制不住的呻吟,她清清楚楚听到文栐杉带着哭腔求她:
操我
求你
潞潞,快一点
干我
徐潞被这声音弄得浑身发麻,摘下耳机平复好心情才重新点开。看完之后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又返回重新看了一遍才确定:视频里的画面都是文栐杉作为享受方的。
换言之,这些视频都是经人为刻意剪辑过只保留了文栐杉在床上的样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