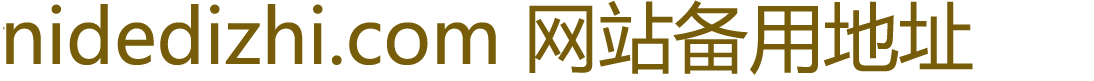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孤勇者(上)
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
我站在喜堂中间,看着侍君被下人扶着跨过火盆进来。
像。
真的是太像了。
红烛摇曳间,新人盖头的流苏闪动,露出我朝思暮念的半张脸,我忍不住低声唤道:“阿宁…”
无人应我。
拜过天地,新妇被人扶进洞房,我与赵政在外间喝酒。酒过五巡,我们都有些醉了。思维不受控制,赵政嘟嘟囔囔地开口:“这一年啊,可真像做梦一样。咱们从表面上的势不两立到现在坐在一块喝酒,这呀,就是人生!跌宕起伏!”他摇摇晃晃与我举杯一敬,再一杯酒下肚,眼神更加迷离;“我先前不明白你何必收这样一个探子进府。但我一看见这个人进来,我就说坏了,怎么那么像裴宁。那会儿要不是他背了你投奔我,现今这府中的正房必是他无疑了吧…”,我脑子里一片混沌,趴在桌上,应声道:“是啊…阿宁…”
裴宁,曾经是我最亲近的…侍从。
说爱人太痛心,说侍卫太疏离,说家奴怕辱没了他,只好叫侍从。
我是爱着裴宁的。从前是,现在也是。
从前在这府里,没有人不知道我爱他,现在,若不是今夜的酒,他的名字已经成了府里的禁忌。
一年之前,正是皇朝更替的时候,朝堂上表面和谐,背后浮潮暗涌。我知晓到了最后一举定乾坤的关键时期,要么跟着皇姐一步登天,要么死无葬身之地。为了测试忠心,我让管家聚集府里的心腹,告诉他们现今情况,想要离开的人可以任意从账房支钱,以慰多年辛苦。
这种时刻自然有人选择离开,但我从未想到裴宁会是其中一员。师爷战战兢兢向我回报说裴宁要从账房支十万两银时,我表面上挥挥手让他拿了去,实际上浑身发冷,发着抖听着暗卫回报他径直赶去拜见了当时表面还是我死对头的赵政。赵政当然不肯见他,他冒着雨跪了一天一夜,终于体力不堪晕在门口,我遣人把他带回后院,看着他烧的发红的脸和惨白的唇色终究还是请了医师来诊治他,安排管家说他若是想离开就随他去,若想要留下便安排他做个不可踏入正苑一步的下等小厮,无论结果怎样都不必禀告。这样细细想来,他予我的最后一面,居然是一副最不堪的病容。
可他明明不该不是这样的。
夜色寂寂,风中充满了露水和丹桂的冷香。我在这样的时刻,突然深刻地怀念一点被裴宁体温暖热的沉香香气。
我曾经赐予过裴宁一串温腻的沉香珠,有时我故意让他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白天再叫他在无人的书房或者花园小径解开衣领拎出珠子让我闻闻味道,那时裴宁总会悄悄红了脸,但从不拒绝;有时他戴在手腕,烛光里我用它束住裴宁的双手,抓住他的手放在他的胸前,叫他自己玩给我看,或者抓着他浸润着沉香香气的手腕用牙轻轻地咬,再用舌尖舔过去,裴宁的身体会在那样的时候轻轻发抖,一声声低声换我主人;还有时我把串珠做一样小小的刑具,隔几颗夹在裴宁的指节,然后使劲握着他的手向中间收紧,裴宁的手并不宽大,却修长,指尖圆润地透出点粉色,像极了女子,每当这样夹完指后,他的指节就会露出动人的红色,我轻轻揉过那些红印,把他拥进怀里,问他知错了没,他总是低头应是,并傻乎乎地请求更深刻的惩罚;还有时……
裴宁,裴宁,我的阿宁。不能念,不愿碰,不敢想。
赵政还在一旁叫嚣着再来对月吟诗,我跌跌撞撞向外,拉开门,跟他说今夜无月,他却已经睡熟了。
我一个人扶着廊柱走下台阶,冷风吹得我酒醒三分,朦胧之中,我看见婆娑树影下有一团暖黄的光。
今日也算是喜事,再不济的下人也可以上前苑厨房去讨碗热酒暖暖身子,怎么会还有人傻傻守在这里当值,当值就算了,新房前还不用个红灯笼沾沾喜气,真是稀奇的很。
于是我开口唤那人:“喂,点灯的那个小奴,你过来。”那团光颤了一下,似乎要被黑夜整个吞噬掉,最终却又慢慢撕裂浓雾般的黑夜,向我走来。
等那光到近前,人跪好了,我把灯笼往上一照,看见那人面容那一霎,我酒全醒了。灯笼几乎要脱手,又怕掉在地上火星溅上地上那人的衣袍,于是被我死死攥住。
是他。是裴宁。
再看到他的那一眼,我心里只有一句:“他怎么瘦成这样。”
他垂着头并不说话,我也沉默。我有些出神地望着他纤细的脖颈,那沉香珠串居然还在,于是我说:“还给我。”他似有些茫然地抬头,一双眼睛望着我。
又来了。就是这样的眼神,从前我莫名其妙朝他撒火或者想要弄他,他就是这样的眼神,像一只迷茫但又想让主人开心的狗,湿漉漉又清澈的眼神,我被这样的眼神欺骗了多久!
我怒从心起,指着那珠串开口:“珠串,我的,还给我。 ”说着伸手就要上去从他颈间把那珠串拽下来。他抓住我的手,却不敢用力,只能哀切地求,说他也是我的,能不能把他一起带回去。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