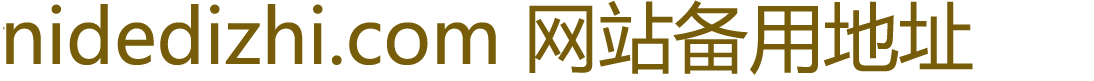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番外 蓬山此去
银馆前的那株老蔷薇顺着栏杆一直爬到秋老板的窗上,支起叉杆,那一簇一簇绯红的花朵乍然跳进眼中,带着晨风春露,开过一茬又一茬。
馆里的少年总抱怨蔷薇太繁茂,夜里虫声吵人,等早起后,也就由着她们疯长,再不提砍了的话。
这些少年也总是待不长的,隔了三五年就换过一批,像是栏杆上的蔷薇,年年有新的容颜。
花香更迭,时光缓缓消磨,秋老板晨起梳发,猛然看见镜中的面容已经有了细纹,细细的一道躲在眼角,他笑,那细纹也弯起,也不知等了多久,悄悄地算秋老板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它。
“哎,真是被他们比老了。”
玉凉倚在窗下折了一支蔷薇,看见他的动作,硬是挤在他旁边,让秋老板看他的眼角,一边笑一边叹,“成了老厌物可怎么办。”
顺手把那枝蔷薇别在他发上。
“你才多大也说这样的话。”
“二十九了,”玉凉低头整理衣袖,“若我当初娶妻生子,现在儿女也要议亲了。”
秋老板愣了愣,也就忘了把发上的蔷薇取下来,和玉凉一起出门,闲话一样提起从前,“我有一个儿子,叫蓬儿,不知会娶个什么样的姑娘。”他日二拜高堂,只有一把空椅放在扁舟身旁,也不知道那个孩子会不会难过。
“不管什么样的,只要喜欢不就是了。”
秋老板笑着摇头,“管不着啦。”
新来的少年站成一排,大气不敢喘地听他们说话,只有一个男孩大概只有十四五岁,抬头冲秋老板笑,唇红齿白眼睛干净,一看就是没有经过世事磋磨的样子。
菡衣问:“你叫什么名字?”
“涯雨,”那少年清清脆脆地答:“无涯的涯,冷雨的雨。”
玉凉奇怪:“怎么叫个这么冷的名?”
涯雨扬唇一笑:“可不就是太冷了,可这是父亲给起的字,说是为了陪另一位父亲。”
涯雨就被留了下来,他好像格外喜欢秋老板,有事没事总爱黏在他身旁,黑豹都挤不过他,喷着鼻子卧在院子里看他卖乖。
新来的少年要先从琴棋书画练起,涯雨站在窗前练字,看着像是聪明的,一手字写的真是太难看,秋老板隔着窗看他,只是那笑越看越促狭,“练了多久了?”
秋老板一袭白色的长衫,与窗外的白玉兰相映成趣,涯雨瞥了秋老板一眼阻止他的取笑,又重新低头练字,脸色半分尴尬也不显,笑眯眯地说:“我自小在深山长大,不曾有人教我写字,现在学起来自然难。”
“昨天还是家道中落的纨绔公子,今天又成了深山鬼魅了,你说你家主人都什么眼光,尽会养白眼狼。”
黑豹呜咽一声,算是回应楚天的不满。
“你这样练不行,我让玉凉找些好字给你临摹。”菡衣只站在窗外和她说话,窗外广玉兰初开,阳光从花叶间穿过洒在他身上,有细碎的光芒跳跃。
“我知道,不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帖子来临,只能先这样。听说老板的字漂亮,有空的话不如帮我写几个帖子吧?”涯雨抬头望了他一眼,又接着低头写字,他挽起宽大的衣袖换了一张纸,袖子里藏着的一朵枯萎的蔷薇就漏了出来。那天菡衣见过新来的那些少年,走到一半才想起发上还簪着朵蔷薇,随手摘了扔在一旁,不知是不是被他捡去了。
少年不再抬头,纸上的字也越写越稳,菡衣盯着他的笔尖,应了声:“好。”
菡衣回去,楚天正坐在他的椅子上喝他的茶撸他的猫。
“你怎么还不走。”
“你怎么回回都爱赶我走。”楚天对玉栖不满到现在,人都离开五六年了还要提出来嫌弃,“前次说玉栖像你自己,这会又说这孩子像故人,我总要来看看临江都有什么样的人。对了你是临江人吧?”
“是啊,你不是知道吗。”那日楚天就是在临江救得他,秋沈两家是临江的百年大族。
楚天叹气:“你有事就爱藏着,我哪知道。”
菡衣推他,楚天不动,只往旁边坐给他腾出半张椅子,菡衣便挤着他坐了,朝楚天伸手,楚天将还剩半杯的茶递给他。菡衣喝了一口,眯着眼睛笑道:“你问什么我没告诉你?”他毫不在意地说,“你要是好奇只管问就是了。”
他前半生那些旧事没什么不可说的,不主动提不过是怕听的人不自在。菡衣拿出诚意要说,楚天反倒不问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可问的。”
“唉楚爷,你还讲不讲理了。”
楚天起身,“我回了,”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正在练字的涯雨,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都是冷的,“那个小孩你自己留意些。”楚天搂着菡衣的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总算搬回一城,大笑着离开。
涯雨聪慧漂亮,见人未语先笑,馆里的人都很喜欢他,今日跟着玉凉学琴,明日缠着玉琉学笑,学了半曲还不成调就要去和菡衣显摆,他又爱撒娇,非要菡衣夸一句才肯罢休。
楚天来的时候他更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