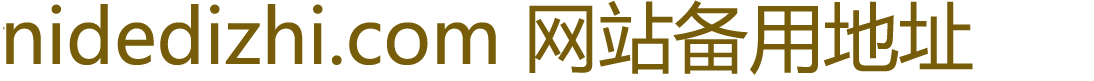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不想连累 yuzh ai wxcò m
晚上,魏知珩洗完澡坐在客厅看转播的新闻。
隔着一扇门,浴室里淅淅沥沥传来洗澡声。文鸢冲干净身体换了条蚕丝睡裙,照例去供台进香。
室内尤为寂静,除了客厅里隐隐约约的新闻播报声,就只剩她拆新香的包装袋动静。
磋地一声,打火机擦油。
听见声音,魏知珩摁掉电视,侧头看她,火光在她脸上忽明忽暗,跳跃得欢快。
“你这几天都去医院了?”
插香的动作一顿,片刻,文鸢恭恭敬敬地插在灰炉处,脊背挺得笔直,头垂着,双手合十念诵。
男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沙发沿,等着她结束。
香雾徐徐上升,空气静得落针可闻,两人甚至能听见对方过重的呼吸声。
良久,文鸢才从垫子上起身,走到他身边恭顺地倒了杯茶递过去:“嗯,毕竟是我们撞了人,正好我也没事做,买了点东西去看看。”
“这样吗。”魏知珩盯着她张合的红唇,微微一笑,“那种地方你还是少去的好。”
“如果你不高兴我就不去了。”
“你想去当然可以去,我只是提醒你要想清楚了。”
镜片下的目光像是在探究着什么,伸手将她搂进怀里,一下一下地抚摸着她的脊背,像是在给猫撸顺叛逆的毛发。
空调的冷气簌簌吹着,文鸢不由得心底发凉。
她抬起脸来,男人摸在肩膀的手捏住她的下巴,一字一句:“如果你中途出了什么事,我该问责谁呢?你说对不对。”
是威胁,也是警告。文鸢听出来了,因为听出来,所以眼底克制不住波动。请记住网址不迷路p ow e nxue19点c o
魏知珩却像没瞧见,手背摩挲着她的脸颊,又轻又柔,耐心十足告诉了她一个道理。
“文鸢,在这个世界上,良心是最没用的东西,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知恩图报。什么人应该帮,什么人不应该帮,心里应该有杆秤,我知道你很懂事,所以,能明白我的话,对不对?”
那些落下来的话轻飘飘地钻入耳朵,他徐徐地引诱着她,表情仁慈,可眼底,文鸢只看见了将人命置之度外的冷漠。
“嗯,我知道。”
对于她的顺从,魏知珩感到十分满意。伸出手掌捧住她的脸,轻轻落吻:“真聪明。”
—
次日。
吃过早饭,魏知珩匆匆出了门。
车子停在酒店楼下,文鸢在窗边目送着远去,思绪有些恍惚。
用早餐时,魏知珩问她晚上想不想一起出去吃饭。提起这件事,文鸢并没给太多期待,顺嘴问了句是跟谁。
很意外,魏知珩竟毫不隐瞒,往餐盘里加了一勺果酱,告诉她是一起吃过饭的外国男人。
文鸢知道他叫基恩先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信息。
提到基恩,她不由得想到了estara。如今estara生死不明,尽管魏知珩告诉她那个女人还活着,可这种把戏哄哄小孩儿也就罢了,她怎么会想不明白?
恐怕estara会被送进一些生不如死的会所里,光是一想,浑身上下像有蚂蚁在啃噬心脏,难受极了。
她不是真的同情,也不是替谁忧虑,而是透过estara提前预知了自己失败的下场。
也许她会成为下一个estara也说不定。
可是,那又怎样?
文鸢深深吸了口气,闭上眼,颤抖着手拉上了窗帘。
半小时后,文鸢在卫生间里洗了把脸,又摸出那些藏匿的钱塞进包里。
站在镜子前,面对面的脸红润却又陌生,她伸出手,缓缓地摸着自己,摸到镜面冰凉凉一片,和她此刻的心情无异。
她十分清楚,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
从三江酒店开出来的车停在103医院外。车上下来个带着墨镜穿着休闲的女人,打着伞进了大楼。
一楼大厅的问诊部人影匆匆,文鸢收起伞,自如地穿梭进走廊摁电梯。
电梯门一打开,熟悉的脸露出来。
空荡荡的电梯里站着个瘦高的身影,看见她的一瞬间同样惊讶了。
洽恩背着个灰色的斜挎包,手紧紧抓住背带,神情有些紧张。
他走出来,身后电梯门嘭一声合上,刚准备越过她,女人向他开口了。
“你要去哪儿?”
洽恩见她不远处跟着的四五个黑衣保镖,知道自己今天不得不回答她,努了努嘴道:“我要去干活了。”
他要去干什么活,那天她都看见了。洽恩没什么好解释的,他们本就没什么关系,扯不上说教。就像以前那些假好心的志愿者过来慰问他们一样,拿着几袋补品就高高在上地把摄像机对准他们因为长年累月干活而满是茧子撮黑的手,说说笑笑地记录他们的窘迫,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