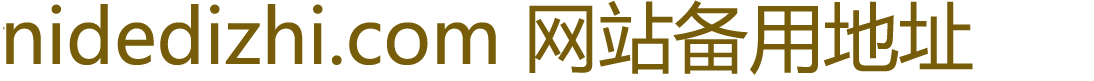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蓝se裙子
—
距离她上船已经过去二十分钟。这趟慢行的跑船到不了柬埔寨,行至金边至少需要一周的水路。可她一心只想快些脱离掌控,怎么可能等那么久?路上会遇见什么事情谁都无法预料,只知道拖得越久,越危险。
驶入湄公河的铁皮船冲着一道道浪花,时不时还有开来开去的快艇和货船经过。船舱内和她一样没有身份的偷渡者都缩在铁皮棚子里睡觉,从开船人口中,文鸢了解到他们从万荣已经走了一趟,这些人有的从菲律宾过来,有的是上游的其他城市,全部都想去泰国,也就是这趟船的终点站,泰国清莱。
船去不了金边,她又上得匆忙,只能站在船上思考对策。
开船的是个五六十岁的胖子,常年在叁地两岸跑走私船,跟副船手换了驾驶位出来吃饭。看见船板上站着个身形消瘦的女人盯着水面发呆,还以为她要跳河,连忙走过来拽她:“妹,你在这里做甚?”
他刚才可见着水面扑腾了几下,不免心生猜忌:“你刚才往水里丢什么东西了?是不是船上偷的?”
文鸢被拽得差点儿摔在板子上,急急忙忙拿刚才地上捡的破布罩住脑袋,只心虚露出两个眼睛:“我没有…只是太无聊了才出来透口气。”
胖子搜寻了一番发现没丢什么东西,于是警告她不准动船上物品。
她点头,不动声色地缩紧了红肿的手腕:“我要去金边,有什么地方能走?”
听她操着一口缅语,胖子狐疑地从上到下睨了两眼。刚才上船他没注意,借着一点儿柴油灯火,这才发现,这女人脸上涂满了唐卡纳,涂太多导致整张脸都是黄色的,生怕人家瞧出来她是什么样。身上衣服破破烂烂也不像个有钱的。
也是了,有钱的谁偷渡啊?早正正经经去坐飞机火车了。
按理说船上的人要去哪,他本不该多管闲事,不过看她这么问了,胖子也耐着性子权当做个好人:“妹,去倒是能去,就是这趟船不走啊,我总不能为了你这么个客专们跑一趟金边吧?那是要绕个大弯。”他意思不划算,除非文鸢掏一船人的钱。
势力的小眼转了转去也没从她身上看见什么金钱味,这句话是故意这么说。去金边,起码一沓子钱,路途休息还得在驿站,赔本的买卖,不划算。
文鸢早知道他会这么说,刚才她在船上就已经问了里头和她同样上船的人,这趟船去不了金边。她也只是想找一个近道下站而已,起码,能压缩一半时间。
“还有别的路吗?”
胖子故意看了看,为难地哎哟一声,“那我还真是不知道,你要有本事自己跳下去游到金边那能成。”
说罢叫她别站船板上那么近,那地方才修好,要是掉下去,湄公河里什么鳄鱼什么水蟒爬上来他可不管捞。
在文鸢愣神的目光中,一撂袖子往另一个厨房舱里走了。
过了会儿,手里端着个碗从里面出来,一出来,看着她还在船板上,稀里呼噜吃面的动作顿住,走到她身边又拽了拽:“进船舱啊,你要害死我,站在这里等会被水警看见我怎么解释?是直接把你丢下去淹死啊。”
天边已经降下帷幕,整条湄公河岸只能听见冲浪的声音,可视的探照灯也只能看见水面黑漆漆一片。
文鸢尽量把自己藏在柴油灯照不清的地方,解释:“哥,我想去金边,我可以把我身上所有带上的钱都给你,我都给你,你告诉我可以吗?”
她当机立断从灰色的破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百元美金递上去,十分恳切地求他。
胖子看见她红肿淤青的手一愣,眼神又从手移到那张钞票,顿时惊怪:“你哪来的钱?是不是偷船上的人?”
这句话问得尖酸刻薄,船上确实有个穿得光鲜亮丽的女人,跟一群人挤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保不齐钱是偷人家的。
从他的眼神里,文鸢读懂了意思。刚才她确实偷偷塞20美金和船舱里的一个女孩儿在厕所里换了身衣服,文鸢都不知该不该说自己装扮得太过,这也许是件好事,也可能带来一丝麻烦。不过便利一定是压过那点儿麻烦的。
“不是…这是我自己挣的钱,我只有这么多了,本来要去金边投奔姐姐的。”
“你是做扶手的?”见她从棚户区里来,手上又都是得了性病一样的淤痕,胖子故意问她。
那岸上一排的铁皮棚子,全是她这么大年纪的鸡婆,穿成这个样,要么是到柬埔寨运毒,要么是卖淫的了。
文鸢被他一问,还没反应过来,胖子立马把钱抽走,凑近仔仔细细地看她的脸,在看见她故意闪躲的样子,心下也知道了。
当鸡婆的哪有乐意人家当面说她鸡婆,看样子是自己偷跑出来的了,他也表示理解,说最心疼这些女人,你看,船上跟你一个样儿的多了去,他一年到头看多了跑毒的,逃跑的,走私的,这点儿不算啥。
说归说,胖子拿钱的手恨不得消个毒,生怕钱染上什么性病。
收了钱,胖子很是爽快:“这样,我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