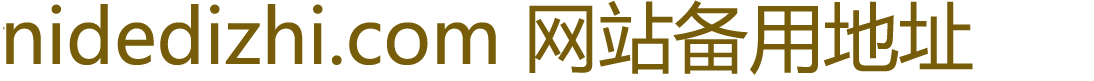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Ⅰ章傲慢(天秤,从来没有真正的平衡?)
&esp;&esp;她的手攥紧成拳,指节泛白。
&esp;&esp;回到办公室,桌上是她与齐溪的合照。
&esp;&esp;她伸手拿起照片,指尖描摹着那熟悉的轮廓。
&esp;&esp;——齐溪。
&esp;&esp;那双眼睛深邃,警服衬得肩线硬朗;眉目间有种不动声色的坚毅,她记得,他笑的时候总会略微低头,声音带着一丝低哑的温度。
&esp;&esp;她自己,照片里的笑容温明亮。
&esp;&esp;乌黑的长发垂落在肩头,衬着一张清秀却坚定的脸。
&esp;&esp;那时的她,相信法律能抚平不公,相信人心仍有光。
&esp;&esp;“齐溪……”她轻声呢喃。
&esp;&esp;她爱他,比对世界的正义还深,比对自己还狠。
&esp;&esp;可如今,正义被撕得满地都是,他还在追查那连续攻击的事件。
&esp;&esp;她明白,他会为真相燃尽,而她会为理想枯萎。
&esp;&esp;照片上的笑容,成了遥远而残酷的讽刺——干净、明亮、带着一点笨拙的甜意。
&esp;&esp;和现在那张脸一点也不像。
&esp;&esp;她盯着那张照片,本应是熟悉的五官,在她眼底却像某种被抽丝剥皮后的伪装。
&esp;&esp;下一秒,那张脸像被撕裂般微微扭曲,仿佛表情控制不住地往某个深不见底的阴影里坠。
&esp;&esp;嘴角抽搐、眼尾颤抖。
&esp;&esp;像是快要露出真正的神色。
&esp;&esp;房间里的灯光晃了一下,突然变得冷白刺眼。
&esp;&esp;砰——
&esp;&esp;窗外爆出一声雷,震得整栋楼都跟着颤。暴雨像倒下的瀑布一样砸在玻璃上,密集到像无数指甲在刮。
&esp;&esp;她的影子被闪电拉长,扭曲在墙上。
&esp;&esp;她望着雨幕,喃喃出声:“如果判无罪说服不了自己,那就改判有罪,但是在司法里找理由减刑,这就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做法。”
&esp;&esp;她记得这是法学院教授说过的话。
&esp;&esp;——这叫人性。
&esp;&esp;白砚站在公设辩护人办公室外,默默站着,像是看穿了谢芷懿。
&esp;&esp;“死刑不过是运气抽牌的问题。”他淡然地说,语气像在陈述一场天气预报。
&esp;&esp;那生杀的权力,被国家赋予在他手里。
&esp;&esp;外头的雷雨像是暴怒的众生,击打着城市的骨架。
&esp;&esp;窗外聚集的群众举着牌子,高喊着正义的名号,声音在雨里破碎。
&esp;&esp;“杀人偿命!”
&esp;&esp;“废死是纵恶!”
&esp;&esp;“我们要公义,不要律师的谎言!”
&esp;&esp;白砚静静地看着那一片人海,神色淡然如水。
&esp;&esp;雨水顺着窗玻璃滑落,如同一行行模糊的经文。
&esp;&esp;——他曾经相信,审判是光。
&esp;&esp;但现在,他更像那盯着人间的审判者,
&esp;&esp;不再问神是否存在,只在问:“如果神不在,那我算什么?”
&esp;&esp;法庭散场后,空气里还残留着冰冷。
&esp;&esp;“谢律。”白砚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
&esp;&esp;谢芷懿转过身,手里的拿铁还在冒着热气,雾气在她指间散开。
&esp;&esp;“白法官。”她礼貌地点头,语气克制,正打算离开。
&esp;&esp;“谢律,”男人语调平静,却带着难以言喻的穿透力,“你觉得,世界上的正义……是什么?”
&esp;&esp;她微微一怔,那一瞬间,时间像被拉长。
&esp;&esp;她的指尖轻颤,咖啡的热气蒸上眼角,却掩不住眼底的冷。
&esp;&esp;这问题她无数次在夜里问过自己。
&esp;&esp;当罪恶被包装成“程序”、当痛苦被归档成“证据”,法律的圣堂是否也早成了虚假的神殿?
&esp;&esp;她想到了阿敏那一具冰冷的十七岁尸体。
&esp;&esp;谢芷懿的手指死死地握着那杯拿铁,几乎要把纸杯捏烂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