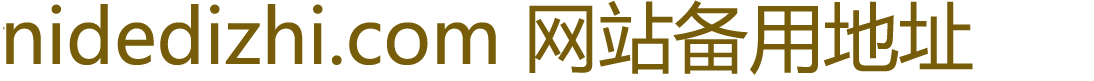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分卷阅读141
入尘道长朝言泓瞪了一眼,言泓回给他一个“你活该”的眼神,入尘道长本就不如言泓双目有神,败下阵来,灰溜溜跟着邢岫烟出去了。
两人走了一段路,邢岫烟回身道:“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罢。出云和篆儿都忙着,不会过来。”
入尘道长拿袖子抹了一把脸,沉吟。
邢岫烟笑了:“道长在我入内之后便一直向我使眼色,莫非是我会错意了。”
咳了几声,入尘道长却挺直腰背,肃穆了神色道:“岫烟,此事在我心中已经积压许久,该不该告诉言泓,我与冰泉老儿久决不下。”
邢岫烟目光一转,渐渐收敛了笑意:“莫非,是母亲那边出事了?”
“唉,真是孽障啊,她回了京城之后,西宁王府便传出太妃重病的消息,就连西宁太妃的手帕交北静太妃想去看望,都被拦了回去。”
母亲虽然身体不好,却也不会一夜之间重病不起,唯一的解释,便是被软禁了。想起母亲离开之前说过的话,邢岫烟握紧了双手。她,大概也料到了这个结果。
入尘道长叹了一口气,继续道:“这几个月,我想尽了办法,数次想去西宁王府中探探虚实,怎奈西宁王把整个王府围得像铁桶一般,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
“原来入尘道长这几个月是在忙着这件事。”
“可惜,一事无成,一事无成啊。”
“西宁王府,母亲?”
两人下了一跳,齐齐往后看,梨树下转出来一个人,几片落叶沾上了他的衣袖,带着木叶的清香。
入尘道长心下暗骂几句,背后已流下一滴冷汗。这言泓睡了几个月,倒是练成了一身深厚内力,饶是他,也察觉不到言泓的脚步声了。这下言泓都听了去,可如何是好。
这边入尘道长天人交战,邢岫烟深深呼吸之后,已经做了决定:“泓哥,你跟我来。”
夫妻两回到寝居,邢岫烟翻出那一本,交到言泓手中:“泓哥,母亲本不欲我告诉你,可是,毕竟血浓于水,于情于理,你都该知道。”
又是一天晨光满。
西宁太妃合上佛经,有静静地念诵一番,方才停止。有人掀帘而入,端了早膳过来。
西宁太妃冷眼看去,正是新来伺候的哑巴仆妇,一张脸死气沉沉的,没半分表情。摆放好糕点粥水,她便行礼出去了,一刻也不多呆。
虽是软禁,西宁王倒是没有虐待她,衣食还是按照原来的份例供给。西宁太妃略略用了一碗粥水,一点小菜便停了箸。
“母妃怎么不多用一些,倒像是本王薄待你似的。”
西宁太妃扯了扯嘴角:“王爷百事繁忙,如何有空过来了。”
“再忙也得过来尽孝啊,本王可是陛下眼中的孝子呢。”西宁王好整以暇地坐在西宁太妃对面,亲自舀了一碗粥:“母妃再吃一碗。”
“有人面目可憎,我看着,吃不下。”
西宁王并不生气,自顾自也舀了一碗粥慢慢喝着:“这粥是王妃亲自下厨熬的,软糯适中,的确不错。”
“王爷慢慢用罢,我就不相陪了。”西宁太妃面无表情起身,却听得西宁王道:“愿为鲲为鹏,遨游于天地之间,这愿望本是极好的,可惜啊可惜。”
西宁太妃只觉得脚底涌起一股冰凉的冷意,顺着她的经脉逆流而上,直冲头顶。
“你,你知道了什么?”
“母妃莫急,他现在好好的呢,和小媳妇舒舒服服过日子。我们兄弟已经二十几年未曾见面了,八成已经见面不相识了。”
“黎成煊,你待如何?”
“无甚,只是想与幼弟见见面,一叙多年兄弟情义。”
“你已经稳坐王位,他只是一介平民。为何,你还不放过他!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母妃,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西宁王喝完了粥,手一用劲,手中碗立时碎裂,散落在地:“卧榻之侧,岂容它人酣睡。我与黎谨烨,注定永不相容。在这世上,我们俩,只能留一个。”
西宁王妃双手的指甲深深陷进肉里,她却不觉得痛楚。心里的煎熬疼痛,让她站不住,跌坐在锦榻上。
西宁王欣赏了一下她的表情,又捏了一块一品酥拿在手里:“本王还有事要忙,改日再来看母妃。”
“黎成煊,你站住!”
“母妃还有何赐教。”
“就此收手,我们两相安宁,否则--”
“否则什么?您要兜我的底么?哦,您重病不出门,外面已经千般变化了。忘了告诉您,北静太妃遇刺,昏迷不醒。您的后招,怕是用不上了。”
竟然连她,也被这孽子算计了么。烨儿,烨儿,母妃该如何护你?西宁太妃一瞬间,面白如雪。
西宁王看到太妃如此,心中是说不出的畅快,唇角一扬,缓步出门、哑妇在身后低首恭送,西宁王淡淡嘱咐:“看紧太妃,别让她死了,好戏开场,缺了她,可就大大地没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