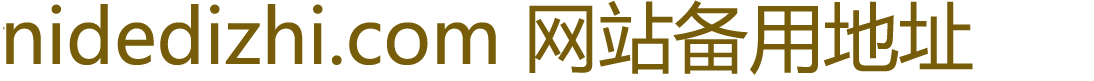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分卷阅读146
昏睡状。
“哈哈,这美人先撑不住了,解了她的丝线,送去王爷那里。”
言泓与入尘道长眼看邢岫烟被背走,心下一急。七苦香趁虚而入,发作更快。两人的眼皮似乎有千斤重,越来越沉,终是支持不住,睡了过去。
仆妇满意地点点头,回身一看西宁王妃戚戚哀哀的神情,道:“王妃,先别忙心疼啊,好戏在后头呢。我先把话放在这里,待会儿你的宝贝儿子作出什么事情来,你可别见怪。”
西宁王妃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只剩一双凄凄双目,流露出了所有情绪。
天旋地转之间,言泓只觉得一脚踏入了一片花园里。周围的小厮丫头来来往往,个个神色惊慌。言泓不觉也受到感染,跟着那一行丫环小厮往前走。
前面早有一个老嬷嬷等着了,斥道:“动作快一些,动作快一些。不知道王妃生子在紧要关头么,若是出了差池,小心你们的皮。”
像是应了她的话,寝居里传来女子痛楚的叫声,还有产婆的鼓劲:“娘娘,您再加把劲儿,小主子就快出来了。”
仿佛有一股大力气推了言泓一把,言泓飘悠悠进入寝居,正看到产婆举着一个满身赤红的孩子,欣喜道:“小主子出来了,是个男的。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婴儿受了拍打,发出地一声啼哭,响亮不已。这啼哭声引来了久候的男主人:“柔儿,辛苦你了。”
“你进来做什么?”王妃虽然累极,但精神还不错:“还未收拾干净,怪脏的。”
“我来看儿子啊。”王爷从产婆手中抱过哼哼唧唧的小儿子,一手握着妻子,脸上挂着愉悦的笑容。
言泓便也心生欢喜,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却觉得心口处有一根筋缓缓磨着,一时间直不起身来。
四周忽地转换,恍惚是匆匆过了数年,那丰神俊秀的王爷,已然步入中年。他静静躺在床上,双目望着帐顶,两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柔儿,煊儿。”他眼珠不曾从帐顶离开,口中却喃喃唤道。
身边一个伏案小憩的年轻人听到了动静,连忙直起身子,握住王爷的手:“父王,煊儿在这里,煊儿在这里。”
“你的母妃呢?”
“母妃她。她太累了,儿臣让她去休息了。”
“不,你骗我。柔儿她是在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烨儿。”
“您已经把那些害弟弟的人都惩治了。人心险恶,您怎么会料到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敢谋害西宁王幼子。”
“都惩治了?”西宁王低低笑了一声,无神的眼光直直地看着大儿子。
黎成煊不觉心头一跳,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父王他知道了,他什么都知道了。旁边的观言提醒道:“世子,王爷该喝药了。”
“是啊,我去拿药。”黎成煊似有醒悟,站起来拿药。那药碗已经放置了一会儿,温度正可入口。
谁知王爷一看到药碗,忽地发起狂来,指着儿子道:“你暗算了烨儿,又来暗算我。呵呵,我养的好儿子啊,好儿子啊!”
黎成煊目色一寒:“观言!”
观言拱拱手:“无妨,外头都是我们的人,只要喂王爷这最后一贴药,就--”顿了顿,手一弹,做了个吹灰的动作。
黎成煊神色稍缓,端着药走近王爷:“父王,喝药罢,喝了药,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
王爷面上的潮红加剧,眼见得即将大行。身上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死死抵住黎成煊的手臂,不让他靠近。
黎成煊看了看天色,沉声道:“观言!”
观言没奈何,只得上前:“王爷,观言得罪了。您不是想念小主子么,喝完了这一贴药,您就可以去照顾他了。”
说罢,轻轻一按,王爷便身体僵直,再也动弹不得。浓黑的药从王爷的口中灌入,王爷目呲欲裂,几欲充血。
言泓勃然大怒,正要上前阻止,却觉得肝脏一股针刺般的疼痛。一股腥甜涌上喉头,被他生生按捺下去。
往后一退,仿佛踏进了泥泞之中。双脚慢慢下陷,越是挣扎,越是沉得快,黑暗没顶,五识皆闭。
在这无边沉寂之时,言泓却放空心神,咬破舌尖,以疼痛换来一丝清醒。
沉睡之前,那仆妇说,吸入的毒气,叫做七苦香。何为七苦?佛曰:“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谓之七苦。”而每一种极端情绪,都牵动着身体的内里。
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方才他经历了七苦中的生与死,引发喜怒二气,果然,肝与心,已然被损伤。
若是这么下去,只怕经历完七苦,自己已经五脏俱损,与废人无异。
为今之计,得收敛心神,在七苦结束前,破开此境。
仆妇在西宁太妃身后,笑吟吟地看着言泓两人在幻境中挣扎痛苦,垂头一瞥,假意惊道:“太妃,您怎么哭了?啧啧啧,可怜天下父母心。哟,言总管吐血了!”
果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