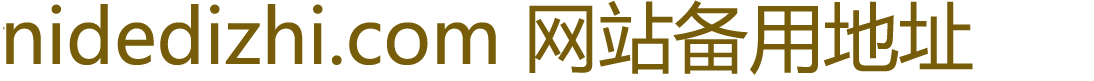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好孩子(R15)
<h1> 好孩子(R15)</h1>
闻霖终于确信,闻渊在刻意躲着她。
这一切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只是她唐突地意识到,原来还没有结束。
他们始终僵持不下。
上小学前,她不过四五岁,连饮食都要闻渊照顾。
父亲频繁去外地授课、参加艺术活动,母亲也是职业女性,除了定时来家里帮佣的阿姨,她和闻渊总是单独相处。
他们经常共食一碗饭,共享餐具、书籍、文具,甚至是同一张床铺。
夜里还会一起洗澡,赤诚相对。
家里的浴缸不大,她的背紧贴着闻渊的胸膛,坐在他身前。
少年闻渊肤色白皙,青蓝的血管沿着他的手背曲张开去;皮肤如同一层不通透的薄膜,水珠在上面滚动,最终沿着下颔清晰的边缘滴落。
独占闻渊这件事,唤起了孩童最原始的冲动。
指向美的憧憬,以及……无法躲避的亢奋。
闻霖学着父亲审视雕塑的模样,用指尖追溯少年肌理的线条,亲吻他下坠的睫毛。
这是唯她才能拥有的人鱼。
她倚着哥哥的身体,想象他是一个盛满了温暖液体的容器。
所有令她贪恋的,要如何才能占为己有呢。
闻渊允许妹妹对自己做任何事。
肉体接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她像迷恋养育者的幼兽似的,用小小的虎牙去戳弄他的锁骨,吮吸早已硬挺的双乳。
无师自通地,发出猥亵的水声。
他握住她湿漉漉的手,借着幼嫩的掌心,轻缓地套弄硬挺的性器。
闻霖模糊地记得哥哥的神色。
混合着冉冉盘旋的蒸汽,他的双眼渐渐变得迷离,却咬紧了下唇。
每一寸肌肤都略微绷紧,重要的是,他是自相矛盾的:不得不遵从欲望,却极力妄图逃脱这种丑陋。他认为自己具有罪。
她着迷地凝视他,伸出小舌,去舔他唇瓣溢出的血。
闻渊搂紧了她,呼吸已然紊乱,很快地释放在她的手里。
“对不起……小霖……对不起……我……”
他总是抽泣着,朝她道歉。她困惑地仰头,去舔他脸上的水痕。
粘粘的,就像从他体内迸发出的热度。
有一点咸。
“小霖是好孩子吧?”
她点头,注视着扣起睡衣的哥哥。他弯腰给她系纽扣,同她说话。
“那就保守秘密,不要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在一起洗澡。啊,对了,为了奖励好孩子,我们去买冰淇淋吧。”
闻霖记得,哥哥露出了只有惯于和大人作交易的孩子才做得出的狡黠笑容。
那是另一个世界。
不存在于地球的任何一处。
多年前的夏日,一栋居民楼里发生的小规模的奇迹。
以致于现在,闻霖仍反复在梦里见证,甚至质疑记忆的真实性——
一方狭窄的空间内,她的哥哥通过沉溺于肉体的欢愉,得以短暂地逃离现实。与此同时,他被抽出了躯壳,成了一种无序幻想的寄托。
她耻于告诉任何人,她对哥哥抱有性幻想。
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哥哥。
因为名为“性”的仪式,他转化为高于人类的存在。
只有祂能够盛放闻霖的欲望。
从来就只有祂。
闻霖抵达餐厅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了。
市郊的山人迹罕至,空中倒是映衬着一些星星。云熙开着他张扬的跑车,驶过环状的庄园车道,在绿植的掩映下消失不见。
长廊里立着沉默的女佣们。
她们上完了菜品,与闻霖擦肩而过。
每个都和她长相几分相似。
闻霖回过头。月光打在被洗练得发亮的大理石瓷砖上,刺痛了她的眼睛。
女佣们则绕过光明,潜入了大宅深处的黑暗。
“闻霖小姐,请。”
她将视线对准目的地,看到严伯打开了一侧大门。
不同于惨白月色,门隙间射出一束辉煌的光芒。
就像是去朝圣的路上,她想。
她慢慢地走过去,驻足光与暗的交界处。
餐厅家具的雕花全是欧式的,墙壁上挂着写意山水画,整体氛围极不协调。角落的雕塑群盖着白布,令闻霖联想到死刑台的裹尸布。
这样的地方,只坐着年轻的主人。
此处唯一的活物。
闻渊的头发比大学时代长了一些,柔软地蜷在耳际。暖橙的灯下,奇异地显出濡湿的蓝色。
他的五官具有纯粹的装饰性。
不如说,闻渊是即使被艺术品簇拥,也绝不会突兀的存在。
暮春时分,他身着米色毛衣,袖口中伸出一截细白易折的腕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