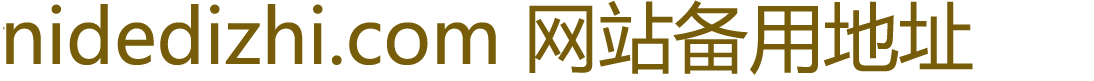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分卷阅读34
起来,从柜子里取出一支烟枪,倒了点碾碎的粉末进去,拿到烛下过了过。
顾钧只道:“此香有安神助眠之用,我看老爷这阵子多梦,跟太医要了几支。”顾钧捧着烟枪来,将香在老爷的鼻前过了过。此香和鸡骨香不同,有些似檀香的味道,萧仲孺吸了一口,过了会子,确觉胸口闷气微微散去,颇是舒坦。
顾钧回到床沿坐着,萧仲孺缓缓握住他的手心,静了须臾,方沉道:“……我又梦到她了。”钧哥儿猜到是谁,却不点破,静静地垂着眸看他。灯火微亮,萧仲孺瞧着那温柔的面目,出神一阵,好似痴了,慢慢支起身来,用嘴贴住了钧哥儿的唇。
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了响,眼看帷帐一松,如轻纱一样垂了下来。纱帐后,顾钧仍坐在床上,萧仲孺说:“我醒来见不着钧儿,心也将停了。”两人贴着面儿,唇密密地亲着,只听顾钧嘶声道:“心停了人就死了。”萧仲孺伸舌舔了舔他的嘴儿,好似那里擦了蜜,手悄声地伸进那柔软的衣服里去:“要真弄丢了心肝去,老爷可真会死的。”
就看萧仲孺的手伸入他裤裆里,揉摸几回,后慢慢深入进去,钧哥儿脸上更加臊红,微微仰起脖子,由萧仲孺在他玉脖上轻轻啄着。他咬了咬唇,声音越发沙哑:“什么死不死的,你劲儿瞎说,我就不、嗯、不睬你了……”
旁人素对老爷恭恭敬敬,唯这顾钧前后如一,只在床笫间调情时别有一种娇姿,不同于平日里那般。萧仲孺向来爱他这般,更加倍疼他,以手指取悦了这娇情儿一番,招惹得钧哥儿如雨打弱柳般浑身打颤,偶有声息从齿缝间流出,而穴里三指进出,又抠又戳,淌出的水都洇湿了裤子。弄了半晌,两人越缠越亲,皆都动欲,萧仲孺温柔地钧哥儿身上的衫子褪去,将人放在身下,只看钧哥儿白白瘦瘦,细腰嫩肤,胸口两点红缨,股间毳毛疏疏,男根半硬,会阴处淫香自发,勾得人挑起玉茎来看,就见那娇弱之处一条缝儿,因生过子了,比起以往似变得窄长,湿津津的,外阴蓬鼓鼓,也是可爱,饶是萧仲孺看了无数遍他,都觉这妙牝甚美。
萧仲孺俯就下来,亲了一口这处,顾钧被他逗得极痒,禁不住笑了。萧仲孺听到笑声,心怕不是要被他给化去了,压下来吻住钧哥儿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美人一笑,如今……我算是明白了。”两人咂嘴亲热,摸着彼此,那硬邦邦的孽具一下下擦着肉缝,轻轻戳出了好些花液,本当顺势进去采撷一番,萧仲孺却起来,由床下取出一个玉匣子。此玉匣子又称宝盒,看上头雕的交媾春画,由此自可猜出里头搁放着何物。只看他从里拿出个套子来,似羊肠所制,外头镶着各种宝石,此淫具名为相思套,用法为套在阳物上,再插进私处,别有一番快活。萧仲孺戴上羊套,拨开钧哥儿的肉瓣,那羊套看着厚,不想插进穴里,仍能传来暖热,钧哥儿先是觉着硌人,可当那一个个凸起碾过去时,整个人就弹了一弹,不禁呻吟出来。
萧仲孺瞧他受用,便安心摏捣,钧哥儿就觉一火热硬具在身子里来回痛痛碾弄,比以往十倍勇猛,哪禁得住,嘶声喘喘不止,淫液一下子淌了出来。萧仲孺一夜里哪只单弄他一次两次,此下就挪到床沿,跟着就将人一把托起来。两人换了换位置,钧哥儿一脚站在脚踏上,另一只屈膝跪在床上,光臀向外撅起,萧仲孺两手箍住他的腰肢,阳具深埋到底,抵住了臀眼。顾钧用手扶在床沿,被他插得鬓发一下一下乱晃,股间阴茎不住甩动,他便伸手将它握住狠命套弄。萧仲孺从后搂着他, 捏过脸来,压了压那翕动的唇:“快不快活?嗯?”钧哥儿吁吁呻吟,身子摇摇晃晃,脑袋乱点:“好……好快活……”
此来纠缠,春风一度,噩梦散去。
顺德六年末。
今年寒冬来得极早,屋里地龙烧着,萧仲孺斜卧榻上,手里拿着一支烟枪。这半年来,他夜里难寐,入冬之后,头疾愈重,只有吸了这口方好受一点。
卢录事走进来,就看太傅慵懒地睁了睁眼:“如何?”卢录事小步走至恩师旁边,将李永达拒不肯议和之事告诉了萧仲孺。
萧仲孺早已料到,却遏止不了怒意,坐了起来,又摔了东西。卢录事噤声不语,这一年来,萧仲孺脾气越发难测,便是他也琢磨不来了。萧仲孺发完了火,就觉很是疲惫,只觉心悸得很,摸了一下额,竟是出了一头虚汗。
他稍静下来,末了,却叹了一声:“你是不是觉得,我糊涂了?”
卢录事猛一抬头,讷讷地说了一句“不敢”。
萧仲孺却笑了一声,他本生得极是俊美,这一笑,竟有几分凄艳。他站了起来,负手走到窗下。昨儿夜里下了雪,一片白茫茫之中,却有几处红艳,原是梅花开了。萧仲孺望着雪梅,又失了神——他这阵子常常往忘东忘西,好似一下子褪了记忆,想是近来杂事缠身,身子也大不好了。
卢录事满脸犹犹豫豫,他这些日子仿佛也寝食难安,最后终是将一直藏在心底的话给说出来。
萧仲孺当他要说什么,听了后却不以为然道:“我也猜是有鬼,可现在,我的身边,又有哪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