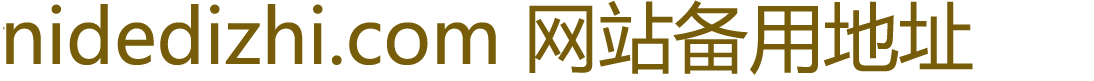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第二折 三姐
可不奉陪了。」說罷掙紮著要起身。
李尚欲念噴勃,哪肯放手,翻身把胡三姐壓在身下,一邊索吻一邊拿手探婦人的裙底。只一探,自覺摸著了一處軟阜,便細細撫摸摳索起來。
胡三姐股間被賊手偷了個正著,嚶嚀一聲,李尚見機吻了上去,吮住了一條軟舌。胡三姐也不再掙紮,香津暗度,動情激吻起來。
李尚在裙內使出了指上的十八般武藝來對付眼前美人,忽的他觸到一粒不及米粒大的突起,暗自迷惑,輕輕用手一撚。只覺得身底下的婦人顧不及口內兩條軟劍的激戰,打心裏發出一聲又長又媚的呻吟,聽得李尚腹下堅硬逾鐵的男根又硬了三分。心想:難不成我撚了她的花蒂子了?哪有生的這般小的?
原來胡三姐的陰蒂本來生的小巧,若不是動情至極不輕易顯露。李尚指上功夫又好,又在這險崖上作這種事,婦人早就十二分的動情了,被李尚這麼一撚,直直小丟了一回,吐出的花蜜塗滿了李尚的手掌。胡三姐身子癱軟,也顧不上阻止男子褪下自己的羅裙了。
李尚著急想看,又扒又拉地褪下羅裙,撐開婦人合攏的雙腿,終於望見了底下的動人風光。
婦人的花唇又白又嫩,真比那豆腐一般。令李尚驚奇的是婦人只在整個蛤口上邊生了一小撮平整柔軟的纖毛,花唇周圍乃至菊蕾處是光潔如鏡,一絲也無。不過李尚心不在此,彎下腰湊近雪阜,撐開花唇去尋那花蒂子。
「哎呀哎呀,弟弟你別瞧哩,好羞人。」婦人拿手去掩都被李尚擋開。功夫不負有心人,李尚終於瞧見了那粒小疙瘩似的花蒂子,粉粉嫩嫩的實在惹人憐愛。
他探過頭去,一口含住,舌頭只顧著在花蒂子上掃來掃去。這下可把婦人美到了,兩腳只顧亂蹬亂踹,口裏呼喊:「好弟弟,好心肝,哎哎哎,可不禁這麼玩的,嗯嗯,哎……」情到濃處又丟了一回。
李尚也是頭次品到女人的花津,只覺得沒甚麼滋味,底下又脹的厲害,只想出來快活快活,於是褪了褲子,放出了那條怒龍肉杵。
胡三姐下面忽然無處著落,心中慌慌的,剛剛小丟了兩回,身子又軟,閉眼嬌聲道:「弟弟你又作甚麼?放著奴家好難受哩。」
李尚笑道:「都是弟弟服侍姐姐,弟弟比姐姐更難受呢。現在就讓姐姐下面嘗嘗屌。」說著扶起肉根在花唇與花溪間逗弄。
胡三姐聽他說髒話,嗤道:「淨是瞎說話,髒了奴家的耳朵,哎喲,怎麼又用嘴去含呢,別玩了,快來疼奴家,嗯……」
原來李尚握著肉杵在花唇間逗弄,馬眼一下含住了花蒂子,玩心頓起,放了又含,含了又放,最後實在忍不住了,道:「姐姐你把衣裳褪了,弟弟就進來疼你。」一邊說著一邊把龜頭在蛤口進出。
胡三姐愈被逗弄花蒂子,裏頭就愈發空虛,心裏瘙癢難耐:「這山上風大,奴家就解了褻衣吧,生怕要著涼哩。」閉著眼把頸後的帶子解了,把兩只大奶瓜袒了出來。李尚看著血脈賁張,扛起兩條細滑白嫩的腿,猛地刺入。
雖然婦人花蜜亂吐,花徑早就潤滑,但是十分緊致,心急的李尚竟然一下子滑了出來,肉根在外面亂顫。
「弟弟心肝,你饒了奴家快進來罷。」胡三姐急的一手揉搓著花蒂,一手去抓肉根子。
「姐姐下面實在緊,滑出來了。姐姐忍忍我這就放進來讓你爽爽。」李尚苦笑,扶著陽具慢慢刺入。
李尚只覺得胡三姐裏頭又熱又滑,探到深處又有圈圈嫩肉包裹而上,實在是美不堪言,只好慢慢深入,細細體會。
胡三姐得了那根混陽鐵杵,舒暢地喊出聲來。沒一會兒就被龍頭頂到了花心,心裏暗喜:沒想到這書生斯斯文文的,竟然有這樣的本錢,得好好采他一回。思罷挺身起來,喘道:「心肝,好人,抱抱奴家。」睜眼一瞧卻是被底下的模樣嚇了一跳。原來李尚的肉根還抵著花心,而露在外邊的尚有兩分,頓時駭然:「弟弟你這下面瞧著嚇人,都頂到奴家的,嗯,怎麼還有半指長在外邊?」
李尚摟著婦人,笑道:「弟弟來讓姐姐好好美一回。」說著底下猙獰的肉根帶著玉脂嫩肉抽動起來。
李尚憋了許久,只想痛痛快快射一回,哪管什麼九淺一深的技法和婦人討饒的嬌喘,次次沒根而入,破開花心,插的胡三姐花容失色,乳瓜亂擺。李尚底下一邊抽插,瞧見兩個雪乳翹然可愛,一手攥著就往嘴裏塞。誰知道剛剛輕吮,一股又膩又甜的汁水噴進了口中。拿出一瞧,淡紫的乳頭上竟然泌著乳汁。
「姐姐你有身孕嗎?怎麼大奶子裏還噴奶水?」說著又就上去吮吸起來。
「哎,哎,嗯,你不能,你不能喝,嗯嗯。」胡三姐次次被插到花心,裏頭酸得花容變色,哆哆嗦嗦地說了兩句。
李尚喝了兩口,只覺著太過膩,幹脆放過了兩個乳球,只用手去揉捏兩個紫葡萄,笑道:「姐姐怎麼這般吝嗇,喝兩口奶水也不肯,待會兒弟弟好好給你些。」
說罷把懷裏的婦人放躺在石臺上,專心破玉穿脂,搜刮頂刺,把婦人的花心捅得又軟又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