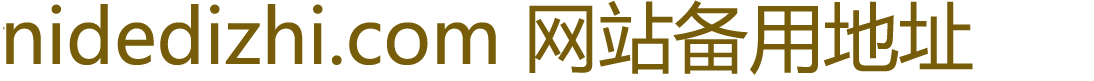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第二折 三姐
胡三姐只覺得身上起了雞皮疙瘩,馬上要丟,嘴裏胡亂叫著「快些快些。」
李尚看著底下的粉人情狀難捱,心想她定是要丟,自己精關也有些松動,似要射出來,於是更加用力,大創大弄了幾十回。胡三姐「哎」的一聲,花口吐出一股子又滑又膩的濁漿,花徑緊緊地抱住了肉根。李尚也忍耐不住,抵著花心子就大射起來。
胡三姐緩了一陣才道:「奴家家裏還有個四個月的兒子,你把奶水都喝光了奴家拿什麼奶孩子?」說到這胡三姐嗤嗤笑了起來。
李尚射完了仍把肉根放在花徑裏,撫弄著乳瓜笑道:「我不剛才還給你了麼,那些應該也夠抵我喝的奶汁了,你又笑什麼。」
「喝了奴家的乳汁,你下面可得硬上三天哩。」
李尚低頭一瞧,剛剛射過的陽具確實沒有疲意,直挺挺地戳在胡三姐的軟膩中。只當她在笑自己,一把抱起婦人,站立著挺動起來:「好姐姐你又笑我,弟弟讓你知道厲害。」
婦人剛剛好丟了一回,還未得休息,又被裏頭次次穿透花心的肉根勾動了欲情,幹脆摟著男人的脖子,貼伏在男人胸口細細受用著。
李尚站了片刻,只覺體力不支,環視四周,瞧見石臺邊上有一處微微翹起的飛簷狀的角,心生一計。婦人掛在李尚身上,正在受用,只覺著男人開始走動起來,睜眼一瞧兩人正站在石臺邊上,底下就是萬丈懸崖。
「你找死哩!怎麼跑這邊來了?」
李尚只覺婦人花徑一緊,深吸了一口氣,笑道:「這邊肏弄起來更有一番風味。」說罷就在邊沿坐了下來,雙腳擺到石臺外,只覺著底下一股大風呼嘯而上,
自己仿佛飛到了空中一般迷醉眩暈。過了一會兒,李尚收回心神,覺著懷中的婦人渾身雞皮疙瘩,連忙把她身上的衣裳裹緊一些,又拿自己的外衣包住,才問道:「姐姐好些了沒?弟弟要動了。」
婦人也不敢拿眼瞧背後的險狀,緊貼在李尚胸前:「你問我作甚?」
李尚得了同意,兩手捏著婦人軟翹的臀肉,抽送插弄起來。
胡三姐剛開始還懼怕著背後的險竣風景,交歡奸淫到深處也顧不得許多,轉過頭來和李尚吻在一起,互度津唾。婦人兩只乳瓜不聽話,又偷偷跑出了衣襟,
緊貼在李尚胸脯前,隨著兩人的抽動軟膩的乳球也一上一下,或扁或圓,擠弄出的乳汁塗抹得兩人胸膛到處都是。
李尚看著眼前的風景愈弄愈狂,胸中積累的氣勢愈來愈高,大吼一聲,把婦人扳過身來。
胡三姐裏頭正被抽送到美處,花徑嫩肉絞著陽具恨不得融在一起,這一折騰,魂兒也差點丟到天外,反手勾住男人的脖頸一動也不動,底下泥濘處不僅花蜜亂吐,還對著崖下淅淅瀝瀝地尿了出來。
李尚哈哈大笑,聳動地愈來愈癲狂,婦人早就無力配合,只得隨他所欲。
李尚兩手握著婦人的沃乳,低頭噙住,狠狠的嘬了一口,然後擠壓揉捏著。
對著空中噴擠著乳汁,貼著婦人的耳邊輕語:「快看,巫山夜雨,真是好看煞人。」
婦人被逗弄得哭出聲來,哽咽著說:「好弟弟別玩啦!快點肏我,肏我。」
婦人的哭狀似在李尚心頭火上澆油,當下依言,轉身把婦人按在石臺上,提著豐臀就是一陣狠抽狂送,次次送到嫩花心裏,逾過百下終於抵著花心把熱流灌了進去。再看那婦人早就不知丟了幾回,癱軟在石臺上動彈不得。
李尚緩緩抽出陽具,見它仍是挺翹堅挺,不知何故。心想:難不成她說的是真的?天下哪有這種奇事?
忽然李尚感覺腳底下開始抖動,逐漸轉至震動,似乎是即將崩塌的前兆。
「壞了壞了,難不成這妝鏡臺竟被我們玩壞了?」李尚心知不妙,抬足就要走。看到一旁被自己幹癱在石臺上的婦人,只好轉身喚道:「好姐姐,石臺要塌了,趕緊跟我走吧!」
腳下晃動愈來愈烈,婦人剛剛睜眼醒轉。李尚直接抱起婦人,誰知突然天崩地裂,石臺就要跌落懸崖,李尚心中苦笑:這下真成了風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