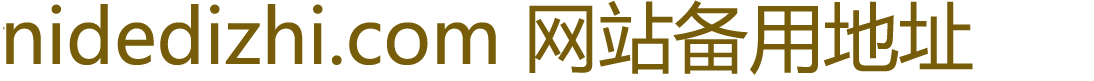
第八章(gaoh)
<h1>第八章(高h)</h1>
那天闹的那一遭使我发了三天高烧,最后还拖着大病未愈的身体考完了学考。李泽言对此表示了小小的愧疚,但在他说一不二的决策者和我的金主大人这两重身份的约束之下,更是傲娇的无法直接的表达出来,于是他开始以送礼物的方式补偿我,短短一周,我收到了许多以前只敢仰望的牌子的衣服鞋子和首饰。学考结束的假期他甚至带我去了一趟法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法语的生疏完全掩盖不住我激动的心情,一路上我像只小鸟一样叽叽喳喳雀跃个不停,他嘴上说着“幼稚”,手上却是牢牢的牵住我,一颗都不曾松开。路过玻璃橱窗的时候我看着倒影里陌生的自己,脱去了中规中矩的校服,镜中的少女穿着一袭墨绿色的半袖连衣裙和一双名贵的小皮鞋,明眸皓齿,长发如瀑,一鼙一笑无不风情。金钱就是力量,短短几天,李泽言就把我包装成了上流社会的女人那样,但一眼就能看出,我既不是财阀的娇公主也不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而是他的,金丝雀。
是的,金丝雀,就是情人。在我委托路人帮我们拍下合影后他们好奇的询问中,我听到了李泽言确凿的答案,要说一直以来我对我们的不正当关系抱有幻想的话,这一刻是真的将其破灭。但我心中毫无波澜,张爱玲说过: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只要他还在我身边,我心头的蔷薇就永远盛开。
后来我把我的心路历程讲给李泽言听的时候,他好奇的问我为什么是蔷薇,我还没说话,小布丁先抢答出声,奶声奶气的告诉他因为妈妈的生辰花是蔷薇。他一把把小布丁抱起来,威胁她如果不早点睡就把她啊呜一口吃掉,小布丁却闹着要听故事,等我们俩终于把这个小心肝哄的睡下后,早就忘了听我说完真正的答案。
我出生于六月十二号,生辰花是野蔷薇,它的花语是浪漫。这个词,契合极了这个男人,契合极了这个故事,更契合极了我十七岁那天的生日。
那天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天,我和李泽言在外消磨了一个晚上,用餐,看演出,在人潮汹涌中接吻。我们回到他别墅的院子里,天上是一轮圆月。我突然心血来潮的想要跳舞,令人惊奇的是李泽言答应了。我们跳的是一支慢舞,一男一女在异国他乡的溶溶月光下舞动着身躯,看上去像一对普通的夫妻。夜色中有一丝凉意,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然后,李泽言说:“你想要做爱吗?”
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月,可我感觉这一生也不过如此漫长,我咬着唇点了点头,惦着脚吻了上去。
我已经忘了我们是怎么滚到床上去,情潮像是洪水猛兽一般把我们吞没,等我分开与他交织在一起的唇时彼此都被对方拨的赤身裸体,他抓过我的脚踝,将两条腿分开至最大,伸出手指埋进我的小穴里,甬道内肆无忌惮抽插的手指滑过敏感点让我微微颤栗。屋里一片漆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月光朦朦胧胧的洒下,在我们的身躯上渡上一段莹白的光。他抽出手指,任我空虚的小穴在空气里一张一合。刚刚被三根手指撑开的小穴又恢复到布满褶皱的原样,李泽言顺着我的脖子一路亲吻向下,然后埋头在我的腿间,伸出舌尖细细描绘著穴口外精致的褶皱。感觉到一个温热之物在自己的穴口外徘徊,我意识到了那是什么,大腿内侧的嫩肉紧张的颤抖起来,伸出手想要去推开李泽言头,“主人……脏……不要……”
我在漆黑的空间里对上李泽言那双布满欲望的眼睛,那里面像是藏着一头猛兽,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殷红的舌尖滑过嘴角,舌尖上还沾着穴口冒著的淫液。彷佛意犹未尽一般,他握住我的手放在脸旁,笑着说:“甜的。”
语毕,舌尖顺著褶皱的位置抵开穴口,一条柔软的舌头滑进温润的穴道。我的小穴本能地开始剧烈的收缩,眼角激情的泪水被宛如电流般窜过脊髓的快感逼落。已经习惯於手指细长的小穴从未经受过如此直接的触碰。光滑细腻的臀肉陷在他宽大的手掌之中,他手指上的薄茧刺激着我敏感的臀肉,让我想被他粗暴的蹂躏。舌头宛如一条小蛇灵活地舔弄著活著的花道,吮吸著花道内自动分泌的淫液。每一次舌头的深入,掐在臀肉上的指尖也会随之用力几分,粗暴却不失温柔的动作在我凝白的肌肤上落下错落的红痕。
我全身的快感全部集中到了下身,只感觉到穴肉挤压过李泽言那条火热的舌头,舌头粗糙的舌苔给敏感的花道带来了密密麻麻细致的快感。我的手指无力的从他脸颊滑落,喉头发出混乱又细碎不堪的呻吟。
舌头模拟著性交的姿势来回在小穴中移动。因为不似手指那般纤细修长,穴内深处的敏感点触碰擦过却不能用力舔弄。穴内深处的瘙痒始终得不到缓解。我被这迫在眉睫的交欢弄得失去了理智,磨蹭着床单来抒发着得不到满足的空虚,“主人……给我……更多……”
舌头离开穴口时脱出一条淫靡的银丝,被玩弄的湿哒哒的穴口有淫液不断争先恐后的溢出。李泽言覆上身,指尖挑开我湿润滑腻的口腔,看着我没有焦距的眼,“舒服